乌托邦小史:是未来蓝图还是1.80传奇新服网?(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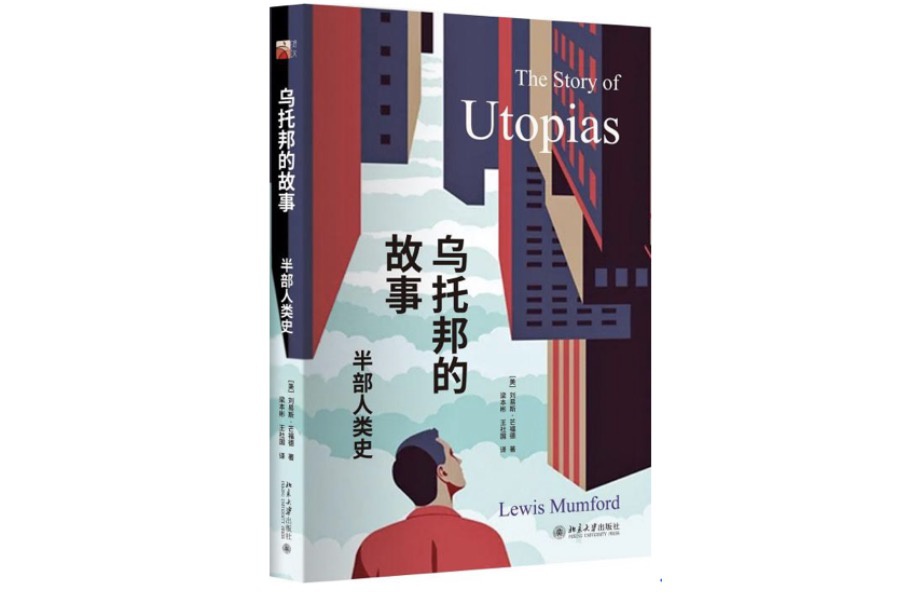
《乌托邦的故事》刘易斯·芒福德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7月
其实,如果依托“乌托邦”一词的含义按图索骥,虽然“乌托邦”一词是正式出现于莫尔的《乌托邦》中,但其实早在人类文明源头的古希腊,柏拉图就已经在《理想国》中勾勒出一座乌托邦的雏形。在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度中,社会的不同阶级分别与不同的美德相互联系,“智慧”对应着城市的统治者,“勇敢”对应着城市的守卫者,而“节制”是所有阶级都应对应的美德,“正义”则是这几种美德诞生的根本原因和条件。每个公民按照自己的禀赋各司其职,维持社会的协调运转。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早期乌托邦作家们勾勒的幻想中的国度在具体设计上有差别,但在政治经济制度、日常生活描写上有着许多共性。柏拉图描绘的“理想国”,其实成为了早期乌托邦作家们想象这些国度的某个“理想型”。在芒福德看来,柏拉图构想中的理想国度其实正是以古希腊城邦为模板。城邦是“他和他的同胞们积极分享的东西,它是一块明确的土地,随便爬上一座山顶都能看到它的边界,生活在边界之内的人,供奉相同的神灵,拥有共同的剧院和体育馆,以及许多共同的利益,这些利益都只有在一起工作、共同娱乐和共同思考的过程中才能满足”。这段话点明了在早期作家心目中,“乌托邦”的核心意旨其实是塑造一种人与人之间极致和谐的状态,一种以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连接为基础的“公共性”。乌托邦的一切制度安排,其实都服务于此。
这种对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以及社会的“公共性”的强调,鲜明地体现在许多早期的乌托邦思想家的作品中。在《乌托邦》中,莫尔就写道,在乌托邦国王初来乍到之前,当地人由于信仰不一而相互争斗、战乱频仍。在国王取胜后,他立马规定每个人拥有宗教信仰以及传播此种信仰的自由。同时规定,在向他人传教的过程中,必须采用“温和文静”的方式,以理服人,绝对杜绝暴力或者诉诸谩骂。“如有人表达自己观点时,龂龂争辩,态度过分激烈,他将受到流放或者奴役的处分”。另一名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在首次出版于1623年的《太阳城》中也曾经写道,在理想国度“太阳城”中,“图像”作为一种用于公民教育的媒介大量出现,城中专门司职教育的首领命令在内外城墙的里里外外和上上下下都挂上美丽的图表。由于太阳城的结构近似于一个同心圆,这些刻在城墙上的图表能为所有公民所见。康帕内拉认为,太阳城的科学文化十分繁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这个城市的制度本身和墙壁上的图画用直观的方法向聚精会神地观看壁画的人们灌输一切科学”。在这里,康帕内拉的话可以解读为一种隐喻:相较于拥有较高认知门槛的文字,图像的直观性对于科普基本的常识其实具有更大的优势,对一种几乎无门槛的知识传播媒介的重视直接暗示着一种对知识的公共属性的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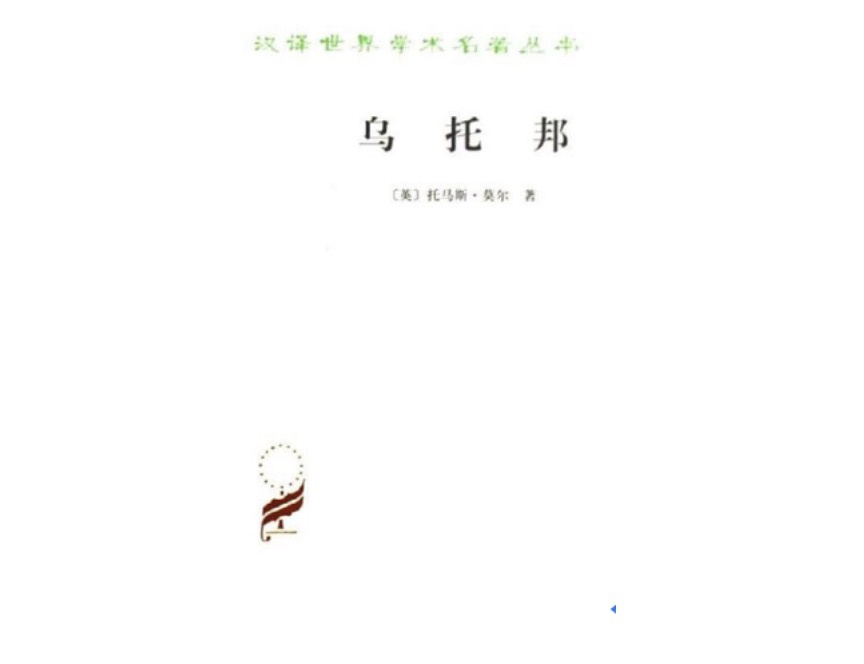
《乌托邦》托马斯·莫尔著,商务印书馆 1982年2月
然而,早期乌托邦作家们身处的时代现实却与他们笔下勾勒的乌托邦是截然相反的景象。柏拉图的《理想国》写作于战败的阴影下,彼时,他所在的阿提卡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场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毁于一旦。而在莫尔、康帕内拉写作的16—17世纪,封建势力依然强劲,资本主义也在西方开始了萌芽,私有制带来的社会不平等已经开始给这些作家们的心灵带来震动。无怪乎莫尔在《乌托邦》中大肆展开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在乌托邦,拥有私有财产是一件不正当的事情。于是在乌托邦人的公共厅馆和私人住宅,粪桶溺盆之类的用具都是由金银铸成,他们也用金银做成锁链戴在囚犯身上。可以说,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充满着冲突与不和谐。现实景象与乌托邦构想之间的落差,让我们窥见人类想象乌托邦一个重要的心理动因——通过想象来逃避令人痛苦的现实,并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批判。正如20世纪俄罗斯著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所言:“乌托邦是人的本性所深刻固有的,甚至是没有不行的。被周围的世界的恶所伤害的人,有着想象、倡导社会生活的一种完善和和谐的制度的需要”。
这种逃避现实的乌托邦想象的确是普遍存在于人类历史的。芒福德对乌托邦故事的梳理局限于西方世界,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同样不乏此类故事。在日本学者武田雅哉看来,晚清至民国诞生的中国早期科幻小说中,就存在大量乌托邦的故事情节。例如,维新变法的主将康有为曾在1913年至1919年间连续刊登作品《大同书》 ,其中就写道:“火星、土星、木星、天王、海王诸星之生物耶,莽不与接,杳冥为期。吾与仁之,远无所施”,表达了一种“世界大同”的乌托邦情结。维新变法的另一员大将梁启超也曾于1902年作《新中国未来记》,畅想“维新五十年大典”,彼时在上海开设了“大博览会”,该博览会:“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
(是谓大同)
,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蔡元培也在1904年写下《新年梦》,在他梦中的这个新世界,人们没有姓名,用编号称呼,没有夫妻的名目,男女两人只要合意,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在公园里定亲。法院和法律不再需要了,同时,整个地球由纵横交错的铁道覆盖,语言已经统一,科技发达到连气候也凭借科学的力量可以自由控制。
在彼时中国内忧外困的时局背景下,这些“大同世界”确实成为了许多知识分子寄托情怀,同时暂时逃避现实忧思的世外桃源。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莫过于1906年由科学会社发行的小说《冰山雪海》。小说中,地球经历了全面的寒潮,连温暖的福建都得日日烤着火炉,主人公们在极寒中感叹世道艰难、社会充斥着不平等,希望出海寻找新天地,一行人在冰山雪海中开道,终于在2399年9月9日于南极建造了一个“理想国”。而时隔9年以后,居住在美洲大陆的犹太人和非洲人也乘船朝南方寻找新的土地,由于同样受到冰山雪海的阻挡,快要饿死时被中国人救到理想国中,他们发觉此时的理想国已是“大同社会”,此后,南纬50度以北完全冰封,人们从地球上各地聚集过来,房屋达到了50万户,其中9成是中国人。联系中国当时的处境,这番颇带有强烈民族情结的乌托邦叙述就十分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