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小史:是未来蓝图还是1.80传奇新服网?(3)

《中国科学幻想文学史》武田雅哉林久之著,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年11月
2
“法郎吉”,民族国家和“雷荷波”:
乌托邦的规划性迷思
芒福德认为:“理念世界的作用之一,就是逃避或补偿。它旨在帮助人们尽快摆脱命中的困境或挫折。其另一作用,则是为我们将来的释放创造条件”。据此,他认为存在两类作用不同的乌托邦,一种是前文提及的“世外桃源”式的“逃避式乌托邦”
(utopias of escape)
,另一类则被他称作“重建式乌托邦”
(utopias of reconstruction)
。“逃避式乌托邦”具有更多的空想性,芒福德评价其“从不考虑任何现实条件的限制,是一系列模糊、杂乱、缺乏逻辑连贯性的图像,这些图像既会让我们激动不已,也会让我们如履薄冰”。相较之下,“重建式乌托邦”则将空想者引向外部的现实世界,这类乌托邦不仅是从宏观上构想世界,而且还切实地考虑了这个世界的设计细节,仿佛在模拟一幅社会建设的蓝图,随时等待被付诸实践。
芒福德曾对康帕内拉同时代的乌托邦作者安德里亚给予高度的评价,在《基督城》一书中,安德里亚为他的乌托邦做了极为精细的城市规划。从产业角度来看,基督城分为三个区域:第一个区域是农业区,第二区域是磨坊、面包坊和肉店,以及所有通过机械而非火来生产的作坊。第三部分是冶金行业、玻璃、砖瓦、陶器等需要连续烧火的行业——这反映了作者所处时代最佳的行业构成,轻重工业层次分明。同时,基督城的学校作为一个微型共和国在运行,在这里男孩女孩平等接受教育,实行自我管理,老师则从全体公民中精心挑选出来。芒福德认为这种模式已经切实出现在了他生活时代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山区的一所暑期学校中。与罗伯特·欧文并列为欧洲“三大空想主义者”的傅立叶也曾在自己的著作中设计出一种名为“法郎吉”的公社组织,在这种公社中,人们能够“一日五餐吃到美味佳肴,哪怕是最贫穷的人,也能够从十二种汤、十二种露珠和葡萄酒,以及十二种肉和蔬菜的调味品中来选择”。而在1841年,一群超验主义者就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创办了类似的一个公社,在这个颇似欧文的工厂实验的项目中,所有的居民需要完成300天的集体劳动,同时享受免费的教育和食宿,吸引了无数达官贵人和乌托邦作家的到访。
随着时间的推移,乌托邦作家们已经开始努力让理想中的国度“照进现实”,并不满足于仅仅让其作为一座太平洋上的虚构小岛而存在,而是事无巨细地安排起社会生活的细节。“重建式乌托邦”反映了人类乌托邦观念的进一步成熟,也呈现出乌托邦观念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对“规划性”的迷恋。例如,从古到今的各类乌托邦作品中,都体现出对社会生活中各类“等级”的严格划分,柏拉图对于治国者、卫国者、平民的划分是典型的一例。这种划分同样体现在科幻作家乔治·威尔斯的《现代乌托邦》中,在“现代乌托邦”中,居民被分为四类:动力型、生力型、基础型、沉闷型。动力型是社会中的活跃元素,包括管理者、企业家和杰出的行政管理者。生力型则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创造性人才,基础型和沉闷型则对应着罪犯、酒鬼等社会底层人士。而在对不同等级的属性进行严苛界定的基础上,威尔斯笔下的这个乌托邦还注册了每个居民的信息,其中包括名字、序号、指纹、居住地变更信息和生活变更信息等,统一都归档到一个庞大的中央档案室中。这些都充分反映出乌托邦思想对“越轨”的担忧和对秩序的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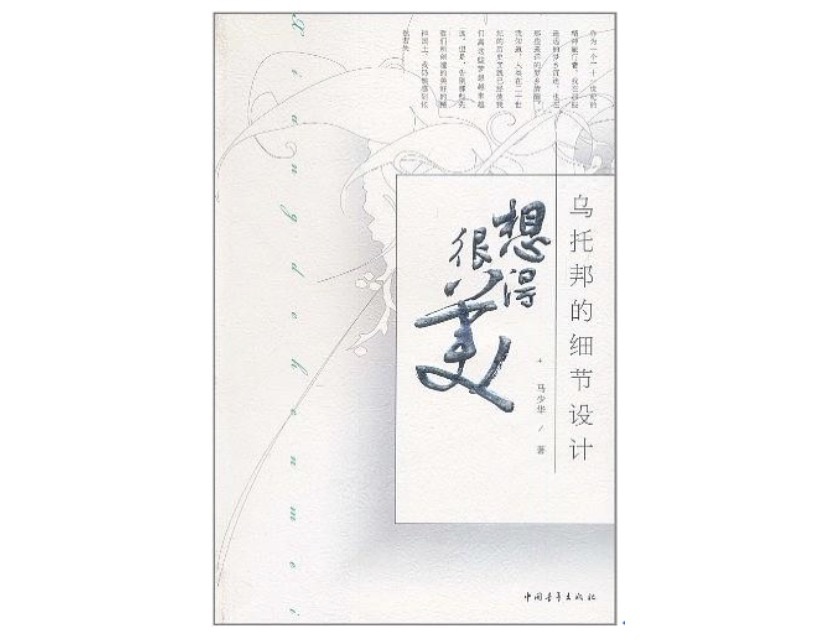
《想得很美:乌托邦的细节设计》马少华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1年4月
值得一提的是,乌托邦观念在人类思想历史中存在十分广泛,它远远不止以这些著名思想家笔下的作品中的面貌出现。芒福德在书中颇具洞见地指出,“民族国家”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存在历史悠久的乌托邦观念,只是在很多时候它被人们视作自然之物。“民族主义乌托邦不承认自然区域和自然族群,而是沿着土地测量员划定的边界圈起所谓的国家领土,迫使该领土内所有的居民都成为一个单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中的一员。”而民族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本身所实施的手段,恰恰反映出乌托邦对“规划性”的极致追求。芒福德指出,民族国家最主要的工具是它的“超级都市”,而都市中最重要的要素并不是地理条件而是其人文景观。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纸张”来完成所有生活和交流的。“对纸张虔诚的关注,是都市居民毕生的事业,日报是人们与生活打交道的工具,小说杂志和画报是他们逃避生活的途径,有了胶片,才有了不需要真人便可上演的舞台。都市居民不必游历世界,因为世界就在他们面前经过,只不过是在纸上。都市居民也已经习惯了从纸张里得来情感体验。”都市中的人类交往是非直接、中介化的,这使得民族国家利用媒介在人们脑海中“制造现实”成为可能。芒福德的这段论述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对民族主义起源与散布机制的论述,在安德森看来,“民族”是现代印刷技术普及之后,在报刊等现代媒介的影响下于人们脑海中形成的“想象共同体”。通过宣传机制,民族主义乌托邦可以让所有的居民培养起相似的品味,“在刚开始的时候,民族主义与乌托邦的居民可能千差万别,但最终会逐渐变得像电线杆一样,完全没有了差异”。作为一种典型的“乌托邦”,“民族国家”不仅作为观念显露出明显的“规划性”,同时它也实实在在体现在了各类民族国家的建设实践中。
乌托邦对“规划性”的极致追求必须以一定的技术作为依托,这似乎可以部分解释科学技术与乌托邦观念长久以来的纠缠。从边沁论述的圆形监狱,到贝拉米笔下的齿轮世界、布罗茨基的戏剧《大理石像》,在各类乌托邦的故事中,科学技术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说这些乌托邦诞生的年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刚刚起步,那么在高新科技层出不穷的当下,依托于技术的乌托邦想象不但并未退潮、反倒愈发繁盛也就不难理解了。在刚刚完结的硬科幻美剧《西部世界》第三季中,一台名为“雷荷波”
(Rehoboam)
的全能机器规划了未来社会每一个人的未来,机器的制造者Serec希望借助这台机器消除因为人类的不完美而导致的混乱,建立一个真正理想的社会。“雷荷波”堪称乌托邦观念对“规划性”追求的极致,而引人深思的是,这个全能机器的剧情设定本身也构成了一种对乌托邦观念的内在反思。在剧中,人类社会的发展被“雷荷波”的剧本牢牢限制,而将这一局面打破的恰恰是从西部世界园区中觉醒的人工智能——一种在剧情设定中超越了单纯的机器和单纯的人类的全新物种。觉醒的人工智能作为一个特殊的镜像,在某种程度上反射出人类这个物种的发展从本性上或许“可以被规划”这一事实,追求“规划性”的乌托邦情结也许从来都是人类自身的一部分。